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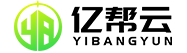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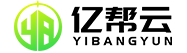

早个十几二十年,年轻人沉迷的魔兽世界玩一个副本要几个小时,后来火爆地成了40分钟的英雄联盟、20分钟的王者荣耀,一局游戏的对战时间越来越短。现下,越来越多的打工人,连20分钟的游戏都玩不起了。
只有玩一局5分钟,随时还能暂停的消消乐类游戏,一局又一局地填补了无力又空虚的碎片时间。这么多年来,它一直风靡,被包装成多种形态,但内核一直没变——以看上去最小的精力投入,诱惑玩家深度沉迷。
凌晨已过,27岁的北漂姑娘郭明帆还没睡。她躺在床上,熟练地点进零点更新的微信小游戏“抓大鹅”——这是她每晚睡前的必备项目,不抓到鹅,“睡觉都有心事”。
玩一局20多分钟,失败了就再来一局,时钟不知不觉走向凌晨两点。黑幽幽的房间里,只有郭明帆的手机还亮着。她精神奕奕,一只手握着手机,另一只手在游戏界面高速翻飞,不时还要配上几个颠勺的动作,把沉在最底下的东西摇上来,三个三个地消除。直到每天的副本通关,郭明帆才心满意足地放下手机。
近一年来,郭明帆几乎都是在“抓大鹅”迎来新的一天。这是一款发布于2024年的三消类休闲小游戏,在年轻打工人里风靡至今,每天都有几百万玩家在线抓鹅。它不需要下载什么App,在微信小程序里一搜,就能直接开玩,继跳一跳、羊了个羊之后,再次刷屏年轻人的社交圈。和它的前辈们一样,抓大鹅的玩法同样简单、传统,有点像是3D版的“消消乐”,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,玩家们只需要在繁杂的物品堆里,找到同样的三个物品消除,直到界面全部清理干净,就算抓到了一只鹅。
最疯狂那段时间,只要抓住一个时间空隙,郭明帆随时随地都能抓大鹅。有时候“命”没了,必须得看30秒广告才能续上,郭明帆反而会长舒一口气——周末,她会瘫在沙发上,一口气玩到中午都无法起身,只能期盼自己以广告为契机,得以督促自己从沙发上坐起来,把外卖先点上。
晚上更是如此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也是人自制力最低的时候,开头的那一幕在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反复上演。深夜,郭明帆喜欢关了灯玩游戏,到了实在熬不住要睡觉的时候,闭上眼睛还全是大鹅的重影。脑子也没停下,郭明帆会对刚刚最后一局复盘良久,甚至在大脑里继续抓起了鹅。
早几年,新闻里沉迷三消游戏的一度是中老年人。比如开心消消乐、宾果消消乐,都是长辈们手机里的常客,吃完饭,家里经常响起“unbelievable”的音效声。这些游戏的标签是简单、低门槛,不需要太多的学习成本,长辈们一旦开始玩,动辄就是几千关,通关升级的决心一点不比年轻人差。
但郭明帆没想到的是,这两年,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朋友们,越来越沉迷三消游戏。抓大鹅里,设置了微信好友的游戏排行榜,她点进去一看,才发现身边一本正经的领导、不怎么交流的男性友人、还有忙着带娃的已婚好友们,都榜上有名。有人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感慨,在无数个无眠的深夜,原来这么多人都在偷偷抓鹅。
其实,三消游戏本就有一个庞大且隐秘的受众群。很多人并不知道,在中国,活跃度最高的游戏其实是开心消消乐。上线亿的月活,超过了王者荣耀、和平精英。
30岁的苏州人苏茗对此深有感触。光是在她家,三消游戏就有三位受众,她、她婆婆、她妈妈。三个女人各有喜欢的三消游戏,苏茗爱玩抓大鹅,最佳成绩是朋友圈前三,到目前为止一共抓了400多只鹅;妈妈爱玩开心消消乐,奋战数年,已经闯到了10000多关;婆婆啥都玩,苏茗形容,婆婆每天“巡回式玩游戏”,像上班打卡一样,零点一过,就依次点开羊了个羊、抓大鹅,全部通关后,再琢磨难度最高的通水管。
年轻人加入后,不一样的新变化是,他们玩三消连App都懒得下载,直接下拉进入小程序就能开玩——这些游戏依靠朋友圈、微信群传播,往往自带病毒般的传染性。郭明帆记得,自己入坑还是在一年前,朋友发来一个复活分享链接,她不过是好奇点了一回,就彻底陷了进去。
集体沉迷“无脑小游戏”的氛围,也好像有一种魔力。前一阵朋友圈的信息流里,总有一个“拆螺丝”的广告,“别笑,你试你也过不了第二关”,评论区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几十个朋友,都在玩梗。
另一个抓大鹅爱好者吴晓珊觉得,年轻人喜欢在小程序上玩三消游戏,一点也不奇怪。在工龄3年的她眼里,这类游戏简直是为打工人专供的。
比如,时间很自由,三消游戏体量往往很轻,想玩就玩,忙起来的时候,几天不玩也没啥影响。不像一些需要肝数值、给人物刷装备的游戏,“像是又找了个班儿上”,两三天不打开,直接跟不上进度。身为游戏爱好者,吴晓珊啥都爱玩,但类似于手游倩女幽魂那样,每天需要上线做任务的重度游戏,是她上班之后首先被放弃的对象。
小程序游戏也精准适配了通勤场景。吴晓珊说,对于每天坐地铁的打工人而言,细节很重要。这些游戏大多数是竖屏,方便她一边玩,另一手还能抽出来抓扶手。她以前还会玩一款叫金铲铲的游戏,但它需要两只手拿着手机玩,在拥挤的地铁上很容易站不稳,尤其遇到网络差的路段,一玩就卡,远不如消消乐来得方便。
最重要的是,它更加适合摸鱼。同样沉迷抓大鹅的90后男生张闯,玩游戏的目的纯粹就是消磨时间。他之前会玩王者、“吃鸡”,但它们开一局都需要一整块时间,还不能随意暂停,稍微掉线一会儿就会被队友骂。更重要的是,手机一横,领导一眼就能看出他在玩游戏,而抓大鹅就可以“随时锁屏,领导走了回来继续玩”,简直是天选打工游戏。
除了抓大鹅,苏茗在微信小程序上玩了不少游戏,但都“一分钱没花”。她说自己很节省,对一切会让她充值的游戏嗤之以鼻。虽然她已经十分沉迷抓大鹅,不过,如果这款游戏的设定是玩一把要一块钱,那她铁定“一次都不会玩”,更别说陷进去了。
而刚好,如今火起来的三消小游戏,最大特点就是不用花钱。游戏里,如果想要获得清除道具,或者“再来一局”,想氪金都没渠道,唯一的方法是观看一则15秒到30秒不等的广告。有的时候,玩一局15分钟的游戏,广告就要看六七个,还无法跳过。尤其是到了一局的关键时刻,尝试10秒钟往前闯关,就要看30秒广告,等待的时间足够叫人抓耳挠腮,求助无门。
▲ 在如今的三消小程序游戏中,为了获得道具需要观看广告。图 / 游戏截图
看得多了,苏茗已经对这些小程序广告如数家珍:腾讯系产品的广告最多,比如腾讯元宝、微信微粒贷,此外就是各种类似小游戏的广告,让人能从一个小游戏无缝衔接到另一个小游戏,简直像个无穷无尽的“三消宇宙”。
有一回,苏茗在综艺里看到,娱乐圈的知名阔太向太也在玩命抓大鹅、看广告。苏茗不免感叹,“我们的时间居然有一天会跟明星的时间等价”,在此刻,小程序游戏居然拉齐了每一个人的起跑线——再有钱的人,也逃不过看广告的宿命。
游戏开发者敖润之告诉每日人物,没办法用钞能力解决问题,是因为这些小游戏属于典型的IAA(广告变现)类游戏,用户们必须通过观看一则又一则广告,为自己的游戏体验付费。而在游戏行业,一款游戏的盈利方式就是三类,除了IAA(广告变现)之外,还有IAP(内购付费),这种模式需要玩家真金白银地往里面充钱,此外就是IAP+IAA(混合变现),内购和广告都有。
可以说,小程序游戏的定位,就是服务于不愿意花钱的大多数。对于婆婆玩游戏,苏茗很支持,觉得婆婆也需要休闲娱乐,不过,这是建立在不用充钱的基础上,“如果是花钱的游戏,那我可能很难说出支持两个字”。
当然,在这个流量变现如此成熟的时代,已经有不少人在三消游戏中,靠他人的注意力赚到了钱。
敖润之介绍,如今,行业里的IAA模式已经非常流行,开发者们能够从最初游戏研发阶段就决定选用哪个模式赚钱。比如,地区就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——如果一款游戏主要面向地区是美国、英国等地的玩家,他们付费能力更强,那么游戏更多会选用IAP(内购付费),而如果是一款面向巴西、印尼这样,用户量大、但付费能力低的群体,游戏就会转向IAA(广告变现)。
小思是一款数独类小游戏的开发者,他的游戏在微信小程序上线。他告诉每日人物,上线几天之后,平台就通知他能够开通“流量主”工具了,也就是在自己研发的游戏里植入广告。而收入的多少,也仅跟用户看了多少次广告有关系。他的游戏体量和受众都很小,日活只有50多个人,看广告的只有几个人,一天收入不过1块钱。
而那些日活高的小游戏,赚得当然就更多。微信小游戏团队透露,截止到今年上半年,已有近70款游戏的日活跃用户超过百万,超300款游戏的单季度流水超过千万元。
这离不开广告的功劳,根据Tech星球,像《疯狂玩螺丝》这样的游戏,用户们会愿意观看一则广告来获得激励道具,比如获取复活机会、关键道具或跳过关卡,只靠这一招,头部游戏的单日广告收入就能高达百万元。
这些需求的爆发,让越来越多更轻、更自由的小程序游戏,涌到了大众面前。今年6月的一次分享大会上,微信小游戏团队宣布其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5个亿。其中最大的功臣,当属抓大鹅、羊了个羊这样的头部三消游戏们。在2022年的一次采访里,羊了个羊的创始人就透露,这款游戏的营收突破了上亿元,团队成员从10人扩充到20人,而游戏的“初始成本才50万”。
回报越丰厚,竞争越激烈。用户不愿意下载、打开App,那么就去更方便他们打开的地方。2024年,坐拥1亿玩家的开心消消乐,就开始了一场从App到小程序的迁移,试图最大化找回受众。
跟短剧、电商行业没什么不同,为了让自己的游戏触达更多人,花钱投流同样是小程序游戏杀出重围的关键。这也是为什么玩家们在小游戏的广告里,总是能看到无数同类型广告、仿佛进入游戏宇宙的原因。
互联网上,每个人的时间都标注好了价格,这话一点也不假。敖润之说,每个潜在用户都自带“标签”,不同的“标签”则意味着不一样的身价。他举例说,“美食”是游戏里十分常见的题材,如果做一款相关主题的游戏,就需要精准标记到有相关行为的用户,比如分享过美食、喜欢做饭,那么,获取这个用户的价格就会更加昂贵。
还有很多行为影响着你的“售价”:泛用户会便宜一些,但假如你已经在某个游戏里付费过,那么,让你看到这类广告的花费可能会贵上10倍。
去年,敖润之参与做的一款休闲游戏最终没有上线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“没钱投流”。那款游戏重视用户体验,从做测试开始,就要花钱买客户,“但没有好的用户数据,就很难拿到新钱”,绕来绕去成了个死结。再加上他做的休闲游戏属于棋牌类,也是很常见的游戏玩法,而“越相似的游戏获客越难”。
至于买量的大手笔客户,还是诸如三七互娱、点点互动、大梦龙途这样的小游戏大厂。去年,打造出《寻道大千》《无名之辈》《时光杂货铺》这类休闲游戏的三七互娱,为了买量,半年就花了53.6亿。根据抖音旗下数字化营销服务平台巨量引擎公布的数据,一款二合三消类游戏的单个付费用户获取成本,甚至可以达到1000元,完全可以用烧钱两个字来形容。
作为休闲赛道里的头部玩家,三消类游戏的回本周期则会更长。敖润之解释,一方面,休闲类游戏的用户付费意愿不强,这要求更高的日活,因此需要花大量的钱去做推广。另一方面,由于玩法简单、赛道拥挤,三消游戏比的是内容量,一款关卡动辄上万关的消消乐,运营、美术、程序等人员配置加起来,团队不会少于10人,这意味着更高的开发周期和成本。
尽管竞争激烈,但对于游戏开发者而言,小程序游戏的确是一片尚可卷入的蓝海。
社交平台上,从零开始学习做游戏甚至成了不少程序员的副业,小思也是其中之一。在他看来,小程序游戏开发简单,不需要版号即可登录平台,是当代打工人寻找“被动收入”(无需花费大量时间、精力就能自动获得)的一种尝试。而根据微信小游戏的数据,目前超过40万的小游戏开发者群体中,超8成是30人以下的小团队。
在转头做三消游戏之前,敖润之其实做的是一款3A游戏,行业里,3A的意思是高成本(A lot of money)、高质量(A lot of quality),高体量(A lot of content),比如去年一经火遍全网的《黑神话悟空》,就是典型的3A巨作,它们的研发周期往往长达数年。
▲ 去年红极一时的3A巨作《黑神话悟空》。图 / 视觉中国
早几年,身在游戏行业,参与制作大型游戏本身就是充满吸引力的事。2022年,入行5年的敖润之也加入了一个刚刚立项的3A游戏,但没想到,刚埋头做了一年,投资方就决定撤资——那段时间,整个互联网经济都在收缩,资方决定将所有的重资产,尤其是还看不到盈利希望的负资产全部清理掉,其中也包括他们还没上线的游戏。
没了钱,整个团队都有点不知所措,只能把消除类游戏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。那时,那款3A游戏的世界观已经搭建好,大家想着,用账上剩余的钱做个休闲游戏,故事还算有得讲。
撑了一阵,游戏依旧没能上线A游戏的开发风险太大,版号难拿,资方容易亏钱,风险很高。而参与游戏的研发人员,不到发布上线那天就没有落地的成果,相当于“两三年的履历都没有价值”。行业的缩水,也让包括敖润之在内的很多从业者只能去做一些短开发的游戏,追求的是“快速”“投入少”“沉没成本低”。
开发者想要更快的生钱途径,刚好,在游戏产业的另一端,那些玩游戏的人,也不想投入更多了。
张闯用一句话总结自己沉迷抓大鹅的原因——很多游戏,他有点玩不动了。他今年30岁,以前最常玩的手游是和平精英和王者荣耀,入坑还是在大学时代,张闯被室友们带着玩,对他而言,玩游戏是为了社交,他挺喜欢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玩耍的感觉。
但毕业之后,一切都变了,工龄越长,张闯玩游戏的频率就越低。最开始上班时,他还会趁着午休的时间,跟大学室友们抓紧开一把游戏,但总是被一个电话突然叫去工作。次数多了,他也没了兴致,随时被打断不仅坑队友,自己也玩得不痛快。
▲ 大学时在宿舍还能常常齐聚打游戏,毕业后则很少有这样的场景。图 / 《别对我动心》
与此同时,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也在下降,很多游戏对反应速度、操作灵活度都有比较高的要求,但前段时间,好久不玩游戏的张闯想“试一把”和平精英,结果发现眼睛根本看不见东西,不管队友怎么说远处有人,他都看不见。张闯尴尬又纳闷:“那就是远方的一个色块,他究竟是怎么认出来有人的?”
玩不动手游,但依旧有休闲娱乐的诉求。张闯开始在闲暇时间抓大鹅、玩斗地主,颇有种“兜兜转转,还是回归无脑”的宿命感——他的境遇,在打工人里不是孤例。简单、解压、随时能玩、投入成本低,成了小程序游戏,尤其是三消类游戏想要精准击中的痛点。
郭明帆也有类似的感受,要从头开始沉浸于一个大型游戏,她觉得太难了。身边,也有朋友爱在游戏机上玩游戏,总是撺掇她一起玩,但那需要买游戏机、游戏手柄、游戏卡带,动辄几千块。手游也好不到哪里去,她尝试玩过王者荣耀,但下载App、初始化等待、走不出去的新手村,成为她无法逾越的三座大山,直到手机内存不够那一天,她直接卸载了。
直到遇见无需任何成本的小游戏,她终于找到了舒适区。郭明帆说,第一次点进抓大鹅,甚至不需要进入主界面,游戏就直接开始了,用社交平台流行的线帧起手开玩”。别的游戏还要种草、体验、新手教学,但抓大鹅这样的小程序游戏,对方根本不需要说话,直接扔一个链接到群里,就总会有人上钩,“距离沉迷只有一个点击的距离”。
张闯记得,早个十几二十年,大家爱玩的魔兽世界,开一个副本要组队、所有人一起玩上几个小时,后来有了40分钟的英雄联盟、20分钟的王者荣耀,一局游戏的对战时间越来越短。现下,连20分钟的游戏都无法满足需求了——最近,王者荣耀也在活动页面加入了消消乐的玩法,赢了可以获得皮肤等奖励,一局也不过5分钟。
一位游戏行业从业者说,重度游戏依旧会有自己的市场盘,但游戏公司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占据年轻人更多的时间,最直接的方法,就是像王者荣耀这样,在重度游戏里加入轻度玩法。某种程度上,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,玩家和开发者们实现了一起追求更快、更碎片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苏茗说,自从开始玩小游戏之后,家庭成员的空档时间都被小游戏塞满了。她会在48分钟的通勤路上全神贯注,力争在路上就通关抓大鹅的主要副本。其余的时间,苏茗几乎空了就会抓一把,孕期排队做胎心监测,抓一把,到了周末,爱玩、爱外出探店的苏茗肚子渐渐变沉,不方便出门了,那就在家躺着,抓一把。
婆婆更是夸张。苏茗生了孩子之后,婆婆全职带娃,会争分夺秒,在孩子睡觉时玩一把抓大鹅,而每到看广告的30秒,她才会俯下身看看娃。
而此前,像张闯这样、曾经被看做重度游戏的主要受众群——男性玩家们,也开始发生转变。敖润之说,这几年,三消行业的一个明显新趋势是,“男性向的三消变多了”。那批沉迷重度游戏的男性用户,也到了精力、体力、时间都跟不上要求的年纪,一些以汽车、维修为主题的三消游戏,随之收获了一批身陷中年危机的男性玩家。
只是,游戏开发得快,玩家们上瘾得快,最终,那股冲动的劲儿消失得也很快。张闯回忆自己的那段沉迷期,刚好是自己准备辞职、大肆摸鱼的时间段。等他找到新工作,几天不玩,这个游戏很快就被他戒断,他形容,“就像风一样,一阵就刮过了”。
郭明帆也是,抓大鹅之后,她又沉迷了几天的“倒水”游戏,把一个罐子里相同颜色的水倒进另一个罐子。但小程序游戏体量很小,很快,所有关卡通关,她顿觉无聊,也不玩了。她身边一位朋友,对抓大鹅不感冒,却对“拆螺丝”相当上瘾,但某一次一个卡顿后再进入系统,苦苦积攒的100多关纪录瞬间消失,只能重新回到第一关开始。愤怒迅速冲上头脑,这位朋友气得直接删除了这个小程序,发誓再也不玩。
用户的欲望或许容易捕捉,却因为种种原因很难留住。一款小游戏的开发者曾经吐槽,自家游戏在短短两周内,日活用户从1200万暴跌至400万。
有的时候,张闯也会怀念自己以前的游戏时间,那是大学时代无课的夏日午后,睡醒午觉,把宿舍里没课的人都召集起来,像进入一个结界一样,沉浸式地玩到夜里,不被任何事情烦恼。即便有什么游戏停服,或者彻底退坑,那也是轰轰烈烈的。绝不是这种,在工作闲暇玩完一把无脑小游戏后,胜利的快感只持续几秒钟,就丝滑地从大脑皮层滑过。
接着,他火速投入新的工作——连游戏后的空虚感都没时间产生。张闯强调说,那绝对不是和碎片化“双向奔赴”,而是向碎片化“被动妥协”。